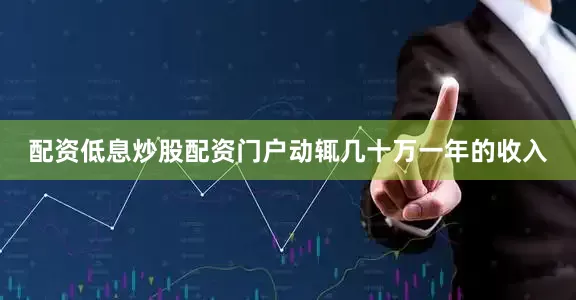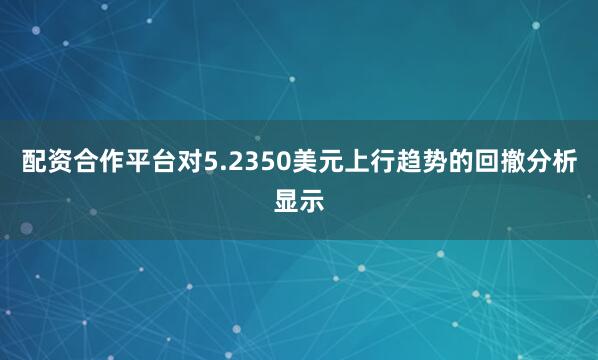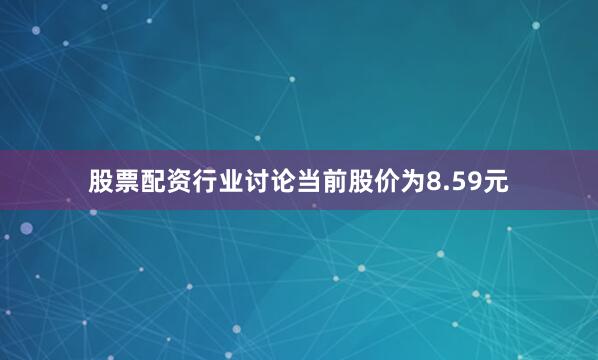小时候老家人常称呼我父亲为“老鹅”,那声音响彻村头巷尾,传得远又悠长。父亲每每听闻,面上便浮出笑容,但那笑却僵硬地凝固在脸上,像一片晒蔫的菜叶子,干瘪而毫无生机,嘴角只微微牵动一下,算是回应。他低头避开目光,脚步仿佛被什么拖拽着,越来越快,仿佛急着要逃开这称谓的围追堵截。
其实父亲名为李鶚。爷爷当初为膝下六位子女取名时,特意都选用了带“鸟”字旁的字眼,这名字是爷爷的希冀,希望孩子们都能拥有飞翔的本领。爷爷是一个有文化的“老私塾先生”。后来我通过不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,才理解了“鶚”字,本是鱼鹰之意,古人更以此比喻才华卓越之人。然而这名字中深藏的期许与重量,在乡间却如坠入无声的泥土里。邻人们大多不识这字,即便偶有识得者,也浑不在意,只图个顺嘴响亮。“老鹅”二字,便如一枚轻浮的标签,轻飘飘粘附在父亲身上,取代了那个本属于他的、饱含深意的名字。
每逢听见有人这样叫喊,我的心里便如被点燃了一束火星,噼啪作响。特别是当村中一群小孩子也像模像样地跟着起哄,喊着“老鹅”,嬉笑着追逐父亲身影时,一股灼热的气流便直冲头顶。羞愤的感觉瞬间胀满了小小的胸膛,我双手握紧成拳,几乎要朝那些无知的喧闹扑过去。
父亲却从无动怒之意。他每每只是停下脚步,脸上的笑容又不由自主地挤了出来,那笑容勉强又脆弱,像是寒冬里被霜打过的最后一片叶子,勉强挂在枝头,摇摇欲坠。我时常看见他瘦削的肩膀在无声地微微颤抖几下,然后便转过身去,继续走他的路,留下那些笑声和那个令人心口刺痛的名字,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空兀自飘荡,像一阵不散的轻烟。
展开剩余62%光阴荏苒,世事变迁。父亲如今已八十二岁高龄,身体尚算硬朗,还在老家耕种二十几亩田地,喂养了两头耕牛。而那个伴随了他大半生的绰号——“老鹅”——竟不知从何时起,悄然消弭于故乡的空气里,再难听闻。变化的源头,清晰可辨:我和弟弟在城市里扎下了根,娶妻生子,而且拥有了自己的车子和房子。这在外人眼中实实在在的“出息”,像一根无形的支柱,稳稳地撑起了我们这个曾经似乎人人都可以任意喊一声“老鹅”、带着几分轻慢与随意来对待的家庭。
而今回乡,乡邻们遇见父亲,称呼已然不同。那一声声“大伯”、“俺叔”,虽未必真懂“鶚”字的高义,却也透着几分自然而生的尊重。父亲听着,依旧笑着,那笑容却不再是当年被霜打蔫的菜叶,而像秋阳下舒展的菊瓣,平静,安然,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释然。他苍老的背影走在熟悉的村路上,再无人追着嬉笑。
名字,从来不是一张随意涂写的纸片。它承载着生命最初的郑重期许,亦如一面无声的盾牌,默默守护着人的全部尊严。那些被轻飘飘喊出的“老鹅”声调,曾像细小的芒刺扎进我童年的天空;而父亲那沉默而隐忍的笑容,却在漫长岁月里教会了我——原来尊严并非总以怒目相向,亦可如深水静流,无声地积蓄力量。只是这深流的尽头,往往需要现实的礁石来证明其分量。
当轻慢的尘土最终被时间与现实的力量吹散,那个被郑重写下的名字——“李鶚”——才真正得以在故土之上稳稳站立。它不再需要争辩,不再需要隐忍,它以最朴素的方式昭示着一个颠扑不破的世情:当你越强大,支撑你的世界,就越显得公平。但是真正的强大以后,并不会去欺侮弱者,只会引领更多弱者变成真正的强者。懂得尊重弱者,才是真的强者,也才是真的能够飞翔的自由人。(文/李多善)
李多善,1980年生于淮河边的、国家级贫困县霍邱新店镇。1996年到合肥上中专学计算机。干过钢筋工、做过新闻工作者,从事教育十八年。2024年自学八个月,一次性通过号称“天下第一考”的法考,获得法律职业资格A证。知名网络作家,庄子心斋,在百度小说、塔读文学、番茄小说、咪咕、喜马拉雅、书旗、七猫等连载《易学大师风云录》、《挣扎在风雨之中》等长篇小说。曾入选“全国网络作家百强榜”。安徽省行知高等教育研究院创始人,安徽庭坚律师事务所律师(实习),中国小说学会会员,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,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,合肥市庐阳区文联委员,合肥市庐阳区书协副秘书长、主席团成员。国家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,文学创作二级。
发布于:安徽省粤友钱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